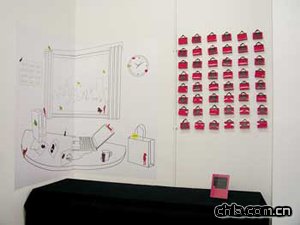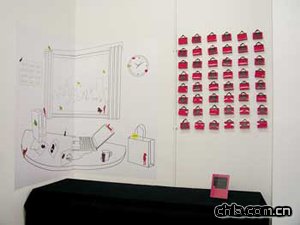
中央美院設計學院2008屆本科畢業作品
“I'm here”出自《圣經》舊約的《以賽亞書》。當以賽亞被上帝呼召成為先知的時候,曾經用這句話作為給上帝的回應:我已經預備好了。眼下,中央美院設計學院2008屆本科畢業作品展的舉辦,意味著這些學生馬上就要離開校園、走向社會,莫非這也是他們的一種自信的宣告: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2008年是北京奧運年,也恰好是現代意義上的平面設計行業在中國恢復的第30個年頭,也是藝術設計作為高等教育的一門“合法”專業在中國正式建立的第10年。2008年還是中央美院90周年校慶的日子。這是中央美院設計專業恢復設立以來所舉辦的第十屆本科畢業作品展。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央美院設計專業從草創到成熟,乃至今天在業內所形成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10年來,設計學院的畢業展也成了一個標桿,以獨特的面貌在國內上百個藝術設計類院校中獨樹一幟,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全國各地的設計專業教師和學生。從2007屆畢業展“07間”開始,更是形成了一個不能被輕易模仿的品牌。
不過設計學院的畢業展其實也在發生著悄然的轉化。中央美院設計系(設計學院的前身)自1995年建立開始,逐漸形成了一套向市場相對封閉的“小眾化”的設計教育路線。這似乎與中央美院這所以純藝術見長的院校自身的性格有著特殊的關系:2003年之前設計系逐漸向全國設計界展示出一種與職業設計教育大異其趣的“純藝術”教學特色,一方面使自己成為一種不太可能為地方設計院校所復制的精英,另一方面對于中央美院設計專業學生“眼高手低”、“進入不了市場”的評價也屢屢出現,甚至還曾有過用人單位不要美院設計畢業生,只認工藝美院的“威脅”。但今天看來,這樣一種學術性設計教育的存在并非是一件壞事。
2003年北京“非典”肆虐的時候,中央美院的設計學科卻正醞釀著一場重大的變革。美籍設計師王敏放棄自己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教職,作為中央美院唯一的一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回國出任設計學院院長。王敏這個被中國設計界幾乎塵封了20年的名字,重新出現在設計界的眼前。王敏的到來,使得中央美院設計學院以一種“設計為人民服務”的新理念向前發展。實際上,這也契合了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潘公凱關于中央美院設計教育定位從精英型到服務型轉換的主導思想。
當“設計為人民服務”成為一種口號尤其是當時一些還不能理解其中真意的設計界內外人士也跟風吶喊的時候,當時一批老設計系的畢業生以及部分教員,實際上有一種非常矛盾的心態:不知道設計系的傳統是否會從此被改寫,是否會徹底打破此前中國高等設計教育中“北方重藝術,南方重市場”的格局。最終,我們看到的是,中央美院設計學院在最近幾年內傾盡全力投入了北京奧運設計的相關項目(而這些在過去都無可推諉地由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承擔)。在社會服務方面,奧運項目為中央美院設計學院樹立了一定的品牌;在教學方面,2008屆才可以說是真正檢驗“設計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的一屆。“I'm here”的主題,似乎也是這樣一種宣告的延續。
事實上,從2003年起,精英型的現代藝術教育和服務型設計教育兩種思想,從未發生過正面的對抗,而只是在內部并行不悖地存在著。2001年開始推行的設計學院工作室制,為這種多元化的教學思想提供了制度的保障。但多元化并不意味著雙方不進行任何的對話和交流。從2007屆畢業展上已經開始透露出的兩種教學思想的互滲和轉化,在2008屆畢業展這里得到了延續。兩種教育思想在對話中正在發生悄然變異,一種對于自己的對立面的變化和融合。對于精英型的藝術教育來說,設計專業招生規模的擴大和實驗藝術系的開辦都對這種思想形成了沖擊,而對于北京奧運會整體設計的介入和參與所取得的成績也不可能不對它產生影響。設計畢竟是一門實務性學科,設計專業擴大招生的一個目的是滿足社會對設計人才的需求,不可能不反過來影響到學院內部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模式。而對于服務型設計教育思想來說,一方面如何針對中國的廣告客戶“自以為是”的心理進行設計素養的啟蒙,另一方面如何以中央美院的特色在國內幾百所設計院校面前脫穎而出,也勢必使得他開始對“設計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進行重新定位。因此,即便是“為人民服務”型的設計教育思想,也在悄然背離著它所被提出的原始語境。
2007年,針對這種詰問,王敏曾經對中國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常務副院長王雪青進行了這樣的回應:通過藝術品位提升整個社會的藝術設計和審美素養,從而在生活中創造美,是在一個更高層面上的“設計為人民服務”的體現。這種回應顯然并不能夠得到王雪青的認同。因為在以務實著稱的中國美術學院,對于畢業設計的要求從來都是“真課題”而不可能是“飛機稿”。然而,這種要求在中央美院卻恰恰是無法也不可能做到的如何在中央美院既有教育模式和特點的基礎上適當朝“服務型”引領,使得兩種教學思想相互吸納、融會貫通,也許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途徑。這是王敏在最近幾年的教學和社會實踐中已經逐漸認識到的。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央美院正在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未因主導教學思想和口號的變化而輕易改變。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兩種教學思想的張力,本身就是設計教育的魅力所在,只有在碰撞和對話的過程中,才能建樹中國設計教育品牌。
認識到這一點,恐怕還僅僅是一個開端。對于央美設計學院乃至整個中國的設計教育,接下來還有一系列的問題等待解決。例如,如何把藝術品位通過對于盈利模式的探討逐漸轉化成一種可以應用于品牌營銷傳播中的商業價值,這一點在央美十幾年設計教育的歷史上一直是一個真正的缺環。很多畢業生在圈內有很好的聲譽,但是卻難以得到商業和社會的認可,這是令教育者真正為難的。其次,媒體環境的轉換,似乎還并未引起設計教育者們充分、足夠的重視。對于新媒體的探討和實驗,其范式轉換的價值,將遠遠比在傳統范式內部的更新更為引人注目。而歷史地看,每年都重復出現的實驗書籍、漢字字體和印刷設計等母體,對于外部來說固然有所新意,但實際在歷年的畢業展中已經呈現出一種同質化的趨勢,這是早就該加以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