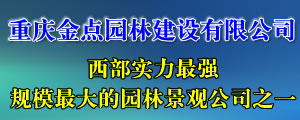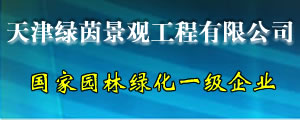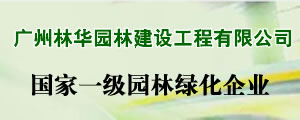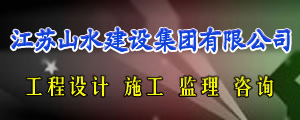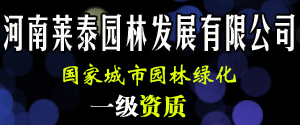| 首頁 → 園林設計|園林規劃-規劃設計頻道 → 理論探索—規劃設計頻道 | www.www.wewon17.com 中國風景園林領先綜合門戶 |
|
生態城市規劃建設與中國城市低碳發展
一、人類聚居的生態失落與生態覺醒 人類住區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人類住區發展史可以說就是一部人類住區的建設史。人類住區發展建設受自然、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在人類住區建設史上,主要有自發建設和規劃建設兩種發展、建設方式。這兩種形式體現在人類住區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從古至今,它對某一城鄉聚居點而言,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有可能是并存的,不同的時期經歷不同的方式或兼而有之,絕對屬于某一類型的城市和鄉村幾乎沒有。這兩種建設方式除受自然地理條件、社會經濟技術條件等制約外,還受到當時當地人們的思想觀念的深刻影響,即人類住區建設實踐活動一定程度上體現其深層次的價值取向,反映人們對理想住區和美好生活環境的追求和認識。由于城市是人類建設活動最集中、最頻繁的聚居形式,對于人類的生產活動、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的影響也最為深刻。因此,我們主要從城市這一角度來探討人類聚居生態思想的歷史演變。 在原始社會相當長的時間內,人類為謀取生存過著采集漁獵的生活,還沒有形成固定的居民點。直到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出現了農業為主的固定居民點,使定居生活成為可能。可以說這是人類住區的最早雛形。隨著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在手工業和商品交換發展的基礎上,社會出現了不從事生產而只經營商品交換的商人,產生了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從而城市也就開始形成,人類住區從此分化為城、鄉兩種聚居地形式。由于當時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技術條件落后,城鄉聚居點分布與規模強烈地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這些城市大都是自然生態條件良好的地方,即靠近河川、土地肥沃、水源豐富等生態條件相對優越的地區,自發考慮了生態平衡的要求,體現了樸素的自發生態思想。歷史上,古老的人類聚居點大都分布在沿海地區、大河流域及其三角洲地區,四大文明發源地均位于此類地區就是例證。 然而,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城市的畸形發展,帶來了城市建設的種種矛盾。如蒸汽機的使用使潔凈的水變成污水,河道成為排污水溝,工業的盲目發展污染了城市環境,環境質量不斷下降;城市在舊的軀體上迅速增長、盲目蔓延、無序擴展,功能布局混亂,工業與居住混雜,居住條件惡化;建筑擁擠、紊亂,缺乏整體環境的考慮,建筑藝術衰退,城市景觀質量下降等,這些在工業革命初期表現尤為突出。工業文明引起近代城市本質的根本變化,自然環境被破壞,城鄉之間舊的平衡被打破,建城實踐活動表現為生態失落。工業革命結束了前工業社會時期城市那種田園詩式的時代。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為資本的壟斷、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使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問題更加加劇,同時城市對鄉村的剝削,使農業到了瀕于破產的地步,城鄉對立已達到很尖銳的程度,引起了為農業服務的中小城市的衰落,大城市工業畸形發展、人口極度集中使土地使用、城市環境等方面面臨日益嚴重的困難。 面對工業革命、城市化對城市乃至人類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和帶來的癥結,有識之士紛紛提出各自的設想、理論學說。英國生物學家蓋迪斯(P.Geddes)在《進化中的城市》(1915)就開始把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應用于城市規劃與建設,將衛生、環境、住宅、市政工程、城鎮規劃等綜合起來研究,強調把自然地區作為規劃的基本構架,還主張城市規劃應為城市地區的規劃,把城市和鄉村的規劃都納入進來,即包括若干城鎮和它們四周的影響范圍,首創了區域規劃的綜合研究。1918年芬蘭建筑師伊里爾·沙里(ElielSaarinen)從大自然中去尋找同城市建設相類似的變化過程,認為城市如同自然界活的有機體,與其內部秩序是一致的,不能聽其自然地凝成一塊,提出城市建設需遵循“表現的原則”、“相互協調的原則”、“有機秩序的原則”,為西方近代衰退的城市找出一種改造的方法,使城市逐步恢復合理的秩序。在城市規劃與建設實踐方面,1911年格里芬(Grififn)的堪培拉規劃在積極引入和強化自然環境與景觀方面進行了成功的實踐。規劃利用地形,把自然風貌同城市景觀融為一體,把自然引入城市,以致堪培拉至今仍享有“田園城市”的盛譽。 歐洲工業革命后的相當一個時期,人們認識不到古城和古建筑的保護問題,20世紀20年代的現代建筑運動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想,也助長了對古城古建筑的破壞。二次大戰后,面對被戰爭破壞的城市,城市的歷史文化傳統受到廣泛重視,戰后一些國家對于有歷史意義的市區往往成片成區地保護起來,甚至整個城市,建設避開古城,另避新城。同時注重對鄉土建筑的保護,也往往是整個村落、整個集鎮地加以保護,而且還包括它們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文化特色的保護,使城市的文化特性、地方文化和歷史文脈的延續性得到保持。聚居生態環境意識的覺醒,從單純的自然生態開始向歷史文化生態拓展。 20世紀6o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城市化的迅猛進程,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能源(主要是石油)危機和環境危機,出現了震驚世界的十大公害事件,面對嚴峻的環境資源問題和生存的迫切性,引起人們對原有生存空間、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反思,進一步激起了人類聚居生態意識的覺醒。卡森(Rachel Carson,1962)的《寂靜的春天》、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Meadows,1972)警示人們世界城市化、工業化引起的全球性問題(人口、糧食、資源、環境等)將影響人類的生存和前景,在世界各地尤其在西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7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城市生態系統列為人與生物圈(MAB)國際計劃的第11項專題,報告建議將城市、近郊和農村作為一個復合系統,并與區域規劃結合,研究大范圍的城市分布格局及城市問題,同時將人的價值觀、創造性、直覺等主觀因素綜合進城市生態系統研究中。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呼吁人們“決定在世界各地行動的時候,必須更加審慎地考慮它們對環境產生的后果”,“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是關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國政府的責任”④,以喚起人類對環境問題的重視。1976年聯合國在加拿大溫哥華召開的第一次人類住區大會(HabitatI)上成立了“聯合國人居中心(uNCHS)”,開始關注包括從城鎮到鄉村的人類住區的發展,并認為“人類住區不僅僅是一群人、一群房屋和一批工作場所。必須尊重和鼓勵反映文化和美學價值的人類住區的特征多樣性,必須為子孫后代保存歷史、宗教和考古地區以及具有特殊意義的自然區域”。1963年希臘學者道薩迪亞斯建立了人類聚居學學科,著重研究城市居民與其生態環境的復合關系,研究城市建設對自然條件、環境質量的作用與反作用,以求全面地合理地解決現代城市面臨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問題,力圖創造適合人類居住和工作的聚居環境。美國的麥克哈格(I.L.McHarg)教授不僅從生態學的外部因素去觀察自然景觀的多種變化,而且把自然環境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去觀察研究,認為人與自然必須是伙伴關系,必須與大自然合作才能使兩者共同繁榮。 隨之,這一時期社會的價值觀念也發生重大變化,城市先進的標準由“技術、工業和現代建筑”演變為“文化、綠野和傳統建筑”,提出回到“自然界”。新時代所提出的環境、文化、游憩、生態等要求不同程度地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區域規劃、城市總體規劃、新城建設、科學城、園林綠化、古城和古建筑保護等方面體現出來。以致古城和古建筑遺產的保護又逐步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城市的園林綠化建設也受到了廣泛重視。而隨著環境概念的全面深化,城市規劃設計和建設不再是停留在單純強調視覺藝術上,忽視人性設計,而是開始轉向注重“人、社會、歷史、文化、環境”,注重對人的關懷和對社會的關注。城市規劃建設采取社會目標的群眾參與,體現在規劃方向、政策和實施過程上的決策參與。聚居的生態思想進一步向社會生態、歷史文化生態發展。而一些發達國家則開始步人“環境的時代”、“旅游的時代”、“文化的時代”,并向著“生態時代”邁進。聚居的生態意識由覺醒開始走向早期的自覺。 進入20世紀80、90年代以來,以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為目標的生態化運動,已在世界范圍內蓬勃展開,并正向各方面滲透。世界范圍的環境保護運動方興未艾,這已成為20世紀末最深人人心的全球性運動。這種思想在工業發達國家尤烈,并從環境保護主義、生態主義發展到政治的派別(如綠黨),它的活動也超越了國家和洲界,全球性的生態環境觀念逐步形成。在新的價值觀指導下,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圍繞著人類生存與發展這一主題,積極尋求一條人口、經濟、資源和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發展道路,探求更加理想的人類住區模式,其中關于“生態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各國相繼走向行動。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的伯克利城召開了第一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與會l2個國家代表介紹了生態城市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包括伯克利生態城計劃、舊金山綠色城計劃、丹麥生態村計劃等,內容涉及城市社會、經濟和自然系統的各個方面,并草擬了今后生態城市建設的十條計劃;1992年又在澳大利亞的生態城市阿德雷德舉辦了第二屆國際生態學術討論會,大會就生態城市設計原理、方法、技術和政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案例;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也舉辦了未來生態城市全球高級論壇和生態城市設計展覽;1996年在西非的塞內加爾舉行了第三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會議進一步探討了“國際生態重建計劃”,1997年在德國萊比錫召開的國際城市生態學術研討會也將生態城市作為主要議題之一,2000年在巴西的庫里蒂巴舉行了第四屆國際生態城市學術研討會,進一步交流了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研究的實例,2002年在中國深圳舉行了第五屆國際生態城市學術研討會,等等。這些有關生態城市的會議不僅促進了生態城市理念的普及與傳播,而且進一步推動了生態城市在全球范圍內的建設實踐。時至今日,人類聚居的生態價值取向已成為歷史的必然,而且認識到“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自然是一個復合大系統的整體,”“必須當成一個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⑨,從單純的自然環境生態取向逐漸發展為更全面的廣義生態觀,包括社會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自然生態等平衡、協調發展。人類聚居已走向生態自覺。
編輯:jojo |
閱讀: 次
網友評論(調用5條) 更多評論(0)
最新推薦
企業服務
|
|
|||||||||